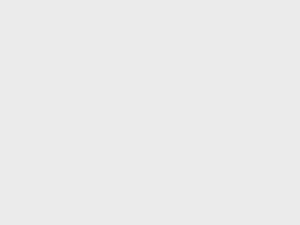(社科院:中国银行业利润畸高,可向实体让利近万亿元)
通过消除高盈利背后的不合理成分,银行可以向实体经济部门让利近万亿,同时能够缓解地方债务压力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风险
文|张斌 朱鹤
中国金融行业是 “高盈利、高薪酬、高纳税”三高行业,高薪酬和高纳税的支撑是高盈利。金融业的高盈利主要来自银行,银行的高盈利背后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不合理成分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缺乏竞争,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银行信贷。
通过消除高盈利背后的不合理成分,银行可以向实体经济部门让利近万亿,同时能够缓解地方债务压力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风险,金融行业的效率也会改善。为防止改革对金融业短期带来的冲击,可以考虑分阶段、分领域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和推进改革,为改革留下时间窗口期,给银行预留充足的时间做内部调整和准备。
中国的金融服务“太贵”
金融业作为一个中间服务业部门,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越高说明其他部门为金融服务支付的成本越高。国际比较表明,中国金融业“过于昂贵”。2017年-2019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的均值7.8%,不仅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出了金融业更加成熟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1%,说明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了昂贵的费用。
这种贵进一步体现为金融业的“三高”特征——高利润、高工资和高税收。利润方面,根据OECD可比数据,中国金融业营业盈余在全部企业营业盈余的占比达到13.7%,不仅远远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高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5.3%。工资方面,我们用银行业人均薪酬/人均GDP反映该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水平,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平均约为5.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3。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平均标准,中国银行从业人员的工资要下降一半。税收方面,中国金融业纳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大部分同等收入水平国家。
金融业内部来看,银行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金融让利主要就是银行让利。2018年至今,银行占全部金融业资产的比重超过90%。银行部门获得高增加值的基础是银行部门的高额盈利。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银行业的ROA和ROE与国际同行相比并不算高,尤其是ROA水平偏低。这说明效率本身无法解释银行的高额盈利水平。
对于银行业高额盈利的一种解释是中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因此银行部门获得了高额盈利。这是事实,但是与同为银行在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德国相比,其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4.18%、3.76%,远低于中国7.8%。日本和德国银行业的人均薪酬与人均GDP之比为1.8和2.2,远低于中国。这个解释不能回答为什么银行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如此之高,不能回答银行获得相对其他行业更高的利润和工资水平。
中国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获得了更高的盈利和单位劳动力平均薪酬,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其不合理成分。银行业的高利润和高工资可能部分来自宏观经济环境、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快的效率提升等,这些是合理成分;高利润和高工资也可能来自各种政策扭曲或者市场失灵,这是不合理成分。因此,金融让利的关键在于找准让利对象和方式,降低不合理成分。
政策红利是银行超额利润的来源
推动银行让利,关键是要搞清楚银行都是从谁身上赚到的钱。这一点可以从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找到答案。
首先看非金融企业部门。
在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流向了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个行业的贷款以短期流动性贷款为主,且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银行可以根据具体企业的状况调整贷款利率。这两个行业是民营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同时也是不良贷款率最高的行业。2010年至今,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在上升。2017年,不良贷款率最高的行业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在4%-5%左右。总体来看,虽然银行可以适度上浮贷款利率水平,但是考虑到较高的不良率以后银行难以从这些行业中获得明显盈利。
除此之外,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基础设施贷款大概也占了三分之一。这部分贷款期限结构长、收益率稳定且不良率极低,是目前银行对企业贷款中最重要的盈利来源。银行对建筑和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贷款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这部分贷款虽然不良率稍高,但显著低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同样是银行重要盈利来源。
然后是居民部门。
近年来,居民部门在银行贷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是银行扩张规模的主要领域。银行对居民贷款占比在持续增加,2019年达到了36%。增量上,2016年以来新增居民贷款与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的贷款增量基本一致。
居民贷款分为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两类。中国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良率极低,只有0.3%,收益率较高且非常稳定,这是银行业当前最重要的盈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贷款也日渐成为银行的重要盈利来源。这部分贷款的不良率虽然偏高,在1%-2%之间,但贷款利率也较高(根据不同抵押条件和贷款人资质,集中在5%-15%区间),为银行贡献了不菲的利润。
综上可知,目前中国银行的主要盈利来自居民贷款、基建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贷款三个部分。其中,居民贷款和基建贷款都是特定政策环境下带来的政策红利,这为银行提供了巨额的超额利润。
一方面,居民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相对利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LPR利率完全挂钩,二套房的上浮标准也受调控政策限制,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方面几乎没有价格手段竞争。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中国银行业从住房抵押贷款中获得了超额盈利。我们选取了主要经济体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然后计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以此大致反映银行的融资成本)的利差。2015年以来,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差显著高于大部分经济体。中国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差均值高出了大概50个-100个基点。如果只考虑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经济体,中国比它们的房贷利差高出了接近100个基点,日本和德国同样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方式显著高于地方债和专项债融资成本,是银行超额利润的重要来源。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其中包括了超过半数的基建投资具有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性质,这些投资获得的现金流收益很有限。来自公共财政预算、地方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的资金远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的需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贷款规模大约在20万亿元人民币。根据估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融资的成本在5%-6%之间,远高于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3.5%左右利率水平。
这种大量依赖银行贷款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方式形成了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双赢游戏”,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资金,商业银行获得了高额利润。如果隐形债务部分对应基建项目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流来维持债务水平,这类贷款对银行来说是一种可选资产。现实中超过半数规模的基建投资以水利和公共设施维护为主,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这类基建投资普遍缺乏现金流支撑,对应的债务可持续性较差,只能依靠借新钱还旧账才能维持。所谓“双赢游戏”潜藏了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来看无论是形成银行坏账还是地方政府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损失最终还是政府负担。
释放改革红利,推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
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放松房贷利率和优化基建融资结构带来的金融让利规模。
引入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充分竞争大致可以降低居民部门5500亿元的利息支出,推动银行让利于民。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大概要高于同期国债利率1.5%左右。同样是银行为主要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只有1.15%左右。
目前,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是按照5年的LPR利率为基准,2020年二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是5.42%,二季度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均值是2.2%,二者利差3.2%。个人住房贷款规模是32.5万亿元。参照发达国家1.5%的平均利差水平,二季度房贷利率下降1.7个百分点,居民房贷利息支出减少5500亿元。
通过政府债券置换银行贷款,大概会降低银行盈利3400亿-5300亿元,并实质性缓解地方债务压力和银行的坏账风险。平均而言,政府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比政府直接发债融资成本高出2%-2.5%。如果将所有银行贷款都置换为政府债券,对银行部门而言,假定银行从过去持有对融资平台的贷款转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利息损失大约为4200-5300亿元。如果将重点放在公益或准公益等将缺少现金流支撑的贷款,那么按照利息保障倍数低于3的标准,对应的地方融资平台企业有1034家,贷款总额约17万亿元。将这部分贷款转为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并由银行持有,银行利息损失大约为3400-4300亿元。
引入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给银行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工具,会倒逼行业内压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整体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进政府投资的融资机制改革,更大范围地使用债券融资替代银行贷款,对银行来说虽然丧失了一部分盈利来源,也降低了银行未来的不良资产率,对银行业的整体经营是拆除炸药包。
改革后的银行业仍能保持相对高的盈利水平和相对薪酬水平。我们上述的估算表明推进上述改革会带来银行对其他部门让利接近1万亿元,2019年商业银行的整体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让利部分会分摊到银行盈利、薪酬和税收多个方面,银行业仍能保持相当水平的盈利。与国际同行相比,让利后的银行业利润在全社会企业利润中的占比、银行业从业人员相对薪酬仍处于高位。
推进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部分银行财务难以为继或者其他形式的风险集中释放。可以避免同时推进多种改革举措,转而采取在某些区域、某些领域局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可以为改革留下时间窗口期,给银行留充足的时间做内部调整和准备。
(作者张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朱鹤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